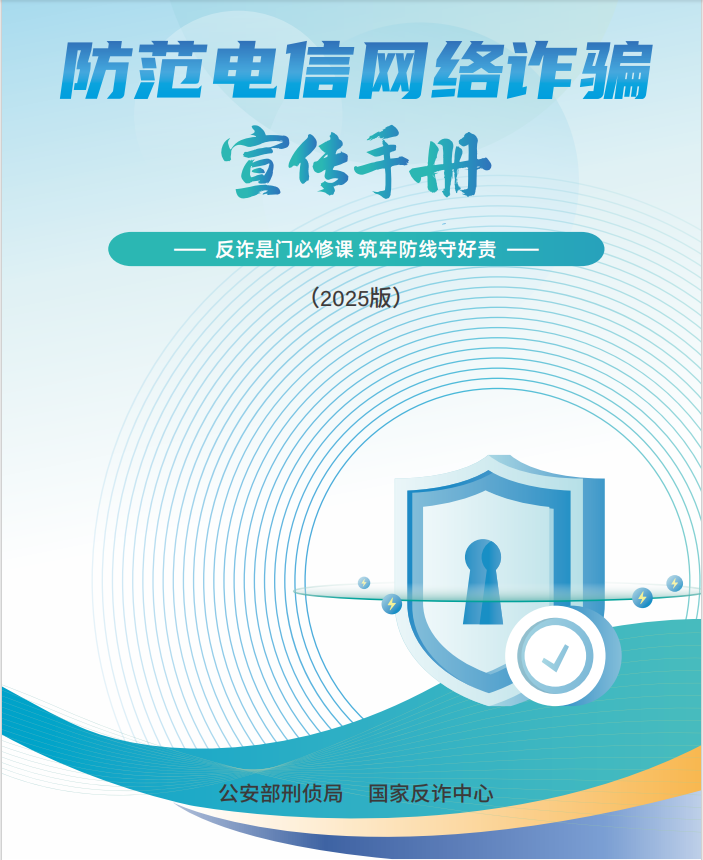我的高考
■ 万洪勇
若论古代发奋苦读的英雄,范文正公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二岁而孤,家贫无依,昼夜苦学”,居然有过“五年未尝解衣就寝”的情况,有时夜晚困倦,就用冷水激脸,以保持清醒,其“划粥断齑”的读书事迹尤为后世所称道。说的是范仲淹曾在醴泉寺僧舍读书,后来为避寺内喧嚣,于寺南一僻静山洞读书,用家中送来的小米晚上一次煮一锅粥,一夜过来成了粥冻子,然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二块,再找点野蒜、野韭菜之类切碎,加点醋、放点盐作为下饭的小菜,如此这般,竟然在山洞里坚持了三年之久。世人从中所见,谅必是范公读书的刻苦艰辛和坚韧不拔,而我更多的是佩服范公极具智慧的学习方法,我以为,范公读书之范式,对莘莘学子而言实在是一个宝贵且可复制的经验。
试想,范宰相当年睡觉尚且不脱衣,遑论叠被子摆鞋子并扫地抹桌这些事体,日常个人卫生所用时间几乎为零,其邋遢的程度当远甚于那位不洗衣服不洗脸的王宰相,而“划粥断齑”,一日两餐,则不啻是简约、低碳的大手笔,将做饭和吃饭的时间压缩至极限,使他能够在卫生和饮食这两件日常要务里省下大把的宝贵时间。只身寄居山洞也是妙不可言,既能完全避开外界的各种干扰,又能在极端不讲卫生的环境下释然自适而不担心影响他人,而且吃得再粗劣也没人来耻笑,穿得再破烂也不会有碍观瞻,无须援引“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之类的豪语以自壮,而能扫却一切心理负担,全身心投入读书求学。
当然,彼时我并不曾知晓先贤们这许多勤学苦读的励志故事,只是冥冥中似与前人略微有些心气相通。我以为,当时第一要紧的是要为千里跃进式的特殊高考想方设法挣得足够的时间,这就必须有勇气、有胆识,不惧人言、不惧碰撞,踩出一条超常规的路子来。饮食和睡眠,课程学习的方式和进度,都可以进行自我规划,可作机动调整和灵活安排。比如说,读书一目十行,自可赢得时间,读得越快时间越有剩余,但是,书可以快读,而老师的讲课是绝无可能快听的,任你一目百行也是徒劳,课程无法快赶猛进,只能一字一板听老师慢慢道来,这就像再快捷的车辆在慢道上也只能踟蹰而行。在课堂上,只好空望着“后山有险路,直通威虎厅”,怎可得“雨夜出奇兵,飞渡鹰愁涧”?还有个人作息习惯的问题,如我,越是夜晚越精神,白天反而精神不振,课堂上老师精彩的讲解往往竟成了催眠的小调。要想发挥看书快的优势,并且顺应夜猫子的特性,则莫若采取自学方式,做学习场上的“独行侠”,那该是何等的耍挎和快意!
单兵作战,装备须得精良,给养必当跟上。我的装备正可谓得天独厚、不用心烦。刚进涟中,我叔叔就给我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定价四块半,赶上涟中半个月的伙食费,相当于淮阴至南京的汽车费。这本工具书太神奇了,里面有着丰富的百科知识,让我爱不释手、大开眼界,我竟然会在一次翻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过程中,无意间根据其中的一个词条,准确诊出自己患了口腔囊肿,消除了思想负担,及时到南门医院作了清除,引来好几位实习医生捧着书在边上对照着察看。更为给力的是,叔叔所在的空空导弹研究院设有培训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购置了种类齐全的优质高考学习资料,有西安的、北京的、株洲的,还有佳木斯的,叔叔每样都给我寄来了。这些资料真的很棒,内容全面系统,表述精炼清晰,能抓住重点、难点,有效扫除盲点,非常适合自学。于我而言,这些高考学习资料就像战场上的决胜利器,让我非常喜爱和受用,也让我乐于与别人分享,有借给同学看的,也有借给老师看的。在“后勤补给”上,我也算得上是得风得雨了,涟中的伙食标准已经比县内的其他学校高不少,我妈又会隔三差五给我捎来肉圆子、食用油和炕饼,甚至还给我捎过自制的猪心罐头;我父亲那当儿小生意恰恰做得很顺手,每次进城都会给我留零钱,我不但可以买点在校园内叫卖的烧饼油条,也可以到饭店买阳春面,还可以买点诸如老舍散文集《我热爱新北京》和电影歌曲集之类的精神食粮。大姐也关心我的饮食,会给我带咸鸭蛋、榨菜之类的小菜子;大姐夫则关心我的穿衣,会将其“退役”的呢制服和皮鞋什么的送给我,让我很早就半洋不土起来。收音机是从小就一直听的,高中当然更要听,对增长高考所需的时政知识有帮助,大哥刚买的涟水出产的渡江牌收音机就被我带到了涟中。经过权衡和推演,觉得自学的事就像曹刿论战所说的那样,是“可以一战”了。
然而,我的自学,意味着要脱离课堂,不受班级的日常管理,班主任和校方能否“法外开恩”予以放行,各位课任老师又会持何种态度,都要打大大的问号,大概率要发生戏剧学上所称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果不其然,马老师态度坚决,无可通融,认为现行教学制度是全世界共同施行的,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过的,是科学合理的,怎么可能为了某个人的喜好而改变;我则讲我的想法和理由,觉得可以从实际和效果出发进行新的尝试。于是我家大哥被马老师约谈,大哥也支持马老师,让我不要异想天开。眼见得我的计划要落空了,要面临山重水复了,但是,我庆幸我遇上的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是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新奇而深刻变化的时代,终于有一天,我等来了一个大惊喜——我们的马老师神情和蔼地向我传达,校领导在详细了解我的学习状况和学习想法之后,经仔细研究和慎重考虑,认为可以因材施教。作为特例,学校决定同意我的请求,可以不上操、不上课,可以忽略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各科老师印的讲义和试题都给我留一份,要求我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后来我从学校图书馆钟老师那里获知,学校对我还有个优待,即“该生”不管借什么书,都可以出借,我因而能借到《人民文学》之类的文艺书刊。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美女同桌也一如那个开明豁达的时代,完全不拘泥男女同学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做派,能够帮我代为打饭,这殊为难得,令我很是感动。
1978之春,郭沫若在北京欢呼《科学的春天》;而我,在1979与1980之交,在涟中,则要欢呼学习的春天了。只是当时我不敢预料、无可想象,在紧随其后的1981,在东湖边上、珞珈山中,武汉大学悄然进入教育改革的春天,老师上课不点名,学生可以不上课,不想读书就去实习,到了考试再回来,可以提前毕业,也可以转系甚至转校。多少年后,人们回甘着发生在武昌的那场脍炙人口的教育改革,称扬着那场改革的操盘手武大校长刘道玉,殊不知,古淮河畔的涟中,领导班子竟有那样超前的思维,做出那个漂亮的决定,像是无形中成了武大教改的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小的涟中倒要比武大还要大一点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