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一面:阿累与鲁迅
■ 李 颖
朱凡(1909-1987),原名朱宗仁、朱一苇,笔名阿累、凡蓉等,涟水县河网乡人,当代散文家、教育家、文艺评论家。他先后在金陵大学附中、上海立达学园、同文书院学习过,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1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同年8月考进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售票员,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鲁迅先生结了一面之缘,成为人生转折点。
扎根上海革命,铸就传奇“一面”
1932年秋的,天空飘着牛毛细雨,秋风带着寒气,等待接班的他,为躲避风雨而走进内山书店。内山书店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2048号,鲁迅在他人生最后9年里,常在这家书店会客,这家书店亦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出售当局禁止的进步书籍。只见他选中鲁迅翻译的作品——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说它写的是“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可是作为售票员,他囊中羞涩,正在窘迫犹豫中,一位日本中年人走过来,他熟稔地将咬着烟嘴的一位中国人喊来。这位先生缓缓走来,告诉他这本书免费,并推荐他买另外一本书——曹靖华翻译的《铁流》。通过交谈才知道这位中国人就是如雷贯耳的鲁迅先生。此后这“一面”成为永恒的瞬间,给予他深挚的人性与温暖。
走出内山书店,告别鲁迅先生,他开始走上革命的远方。他领导上海英汽工人大罢工后,为掩护黑名单上的同志,被国民党沪西区曹家渡公安局逮捕,并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5年。当时他的祖父朱同寿,光绪丙子科举人,选授靖江县训导;父亲朱际云,清廪贡生,任淮涟泗清乡总办等职,对他既恨又怜。于是家里找到同乡顾祝同说情,最后,他关了两年,交保出狱,同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出狱后,他拒绝家里安排,毅然下南洋,任教马来西亚吉隆坡一所中学,后因参加当地爱国学生运动,被英殖民当局迫令出境。
1936年8月,他在陶行知先生帮助下,重返上海并重新入党,与作家张天翼、陈白尘等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他与同乡陈白尘是莫逆之交,两人都喜欢戏剧,更热衷学潮。上海人喜欢叫“阿”什么,从此他拥有“阿累”等笔名,并撰写不少文艺评论、散文,还从事翻译。例如他和欧阳山主编《文化月刊》《小说家》,和艾思奇创办《少年丛书》《大家看》等。同年10月19日,文坛巨星鲁迅先生病逝,举国上下一片悲痛,有成千上万市民和学生为他送殡,其葬仪由生前好友和中外文化界进步人士料理,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等13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后在治丧委员会下成立“治丧办事处”,其职责除执行治丧委员会指定的各项重要任务外,还负责接待来宾、布置灵堂、收受祭品、接见记者等事务性工作,这个组织由巴金、张天翼和他等三十余人组成。
1936年11月的一天,张天翼告诉他,黎烈文主编的《中流》要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专号,向他约稿。起初他感到为难,纵然青年时代崇敬先生,但和先生本人并无密切来往。他最后以《一面》为题,写下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文章最初发表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之“哀悼鲁迅先生专号”上,翌年10月,被收入《鲁迅纪念集》。新中国成立后,《一面》编入大学和中学语文课本,滋养哺育好几代中国人。诚然,此后回忆和纪念鲁迅文章数不胜数,其中范围最广、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署名为“阿累”所写的《一面》。
1939年,他以“凡容”笔名翻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鲁迅是一把宝剑》,原载《文化月刊》,在当时文坛影响很大。鲁迅逝世后的上海左翼文坛一时冷清,茅盾先生在组织“月曜会”,每次他与沙汀、艾芜、王任叔、端木蕻良等人都积极参与,“月曜会”开始于1937 年春,结束于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
“阿累”的一面与多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任战地服务团特支书记,在陈毅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作;1938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他赴大别山参加工作,主编《文化月刊》。皖南事变后,他到津浦路新四军二师所在地参加工作,后调任苏北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江淮日报》主编,不久,调任淮海行署秘书长。1943年3月,调任涟水县县长兼任敌工部部长。他还与刘少奇、粟裕、张劲夫、李一氓、王阑西等一大批党和军队领导人,以及革命文化人有工作关系和友情。期间,好友陈白尘特地撰写《岁末怀朱凡》,表达对他的关心。1948 年9月,他担任中原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学术刊物《改造》编委会主任;1949年4月,任武汉大学军代表,8月任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因搭乘一辆煤车返校,被颠下来,造成脑震荡。
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多面手,为中国文教事业发挥余热。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调任武大,他调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4月,湖南大学被撤,原址成立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他任湖南师范学院筹委会主任;1958年5月,湖南大学恢复,派他主持筹备工作。湘江之滨,岳麓山下,他全情投入湖大办学,为培养国家人才一片赤忱,且有广阔胸怀和党性原则。他曾说:“只要革命信念坚定,需用的人,就可以用。”1959年夏,他到武大找李达,谈及系所缺乏骨干教师和学术带头人,请求支援,李达当即答应。李达对他说:“我是要回湖南、回岳麓山的……你能把湖大恢复起来,我把图书给你。”他也向李达保证:“我有毛主席(题写的)这个匾,一定要把湖大办好。条件再差,困难再多,也要把湖大办起来!”李达还写信给学生吕振羽,希望他参与湖大建设。据《吕振羽年谱》记载:1962年12月1日上午,湖南大学校长朱凡陪同吕振羽,并顺带游览岳麓山,凭吊蔡锷。“文革”之后,继续出任湖大校长;1982年6月,74岁高龄的他退休,闭门写作,同时专心调理身体。198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50周年,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他,以重病之躯,写下人生最后一篇文章《回忆与纪念》,记叙他与左联作家筹备鲁迅先生葬礼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先生最后的敬意。此文收录《文学月刊》,1986年第10期。
1987年1月8日夜,他真的累了,去追随只有“一面”之缘却终生难忘的鲁迅先生。由《一面》改编的连环画《鲁迅赠书给青年》至今仍在上海的鲁迅博物馆内收藏。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在谈论和研究该文的作者“阿累”,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朱凡;他的风范也长存于麓山湘水之间,长存于湘江学子心中。2009年,涟水县创办江苏省第一家村级名人纪念室——阿累纪念室;2016年江苏省全民阅读领导小组推出“中国涟水·首届阿累读书节”。凡此种种,是对其最好的缅怀与致敬,感谢他为中国文坛奉献出最好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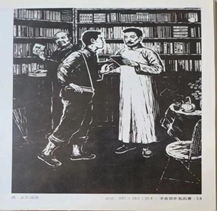
人教社1987年版初中语文第一册(1988-1992年使用)





